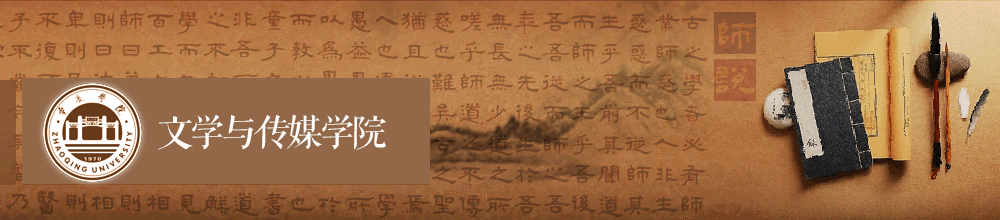(永利集团 yl8cc永利官网, 广东肇庆 526061)
摘要:以夏承焘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教师们的教学思想、讲课风格和时代风云有着密切联系。在教学思想方面,我们着重就其寓教于乐的角度切入,探讨当时教师教学思想中快乐的因素,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讲课风格方面,我们尤其注重当时教师们平易乐观的禀赋特征,并将其与时代氛围和那一时期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探讨,力求公允地评价这种教学思想、讲课风格在当下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夏承焘 教学 讲课 寓教于乐 时代
关于一代词宗夏承焘与词学研究、词学创作的关系,通过施议对、钱志熙等学者的研究,已为人们所关注。但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关系密切的夏承焘的教学思想、讲课风格,同样有着很明显的启蒙色彩和时代特征,至今未见有人提出来并加以专门阐述。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关系到我们国家新时期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和人格个性的评价问题,要是不认真去梳理阐述,给以允当的评价,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及许多有价值的教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有蒙尘、遗珠之憾。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作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最显著的教学特点就在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出圣人悦于学而乐于教的教学风格。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时代的教师们,基本上是熟读精研《论语》一书的,故他们在教学风格上大都能继承与发扬孔子“寓教于乐”的教学特点。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太重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重视类比联想,由类比而启发学生思考,教学相长,学习范围宽广,直觉性强,注重通过学生的感受来引起思考。我们在探索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时期教师教学风格时,亦特别注意运用类比联想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教学风格与我们目前教育界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教师“寓教于乐”的教学风格包括了他们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几个方面。我们准备分为三部分来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从夏承焘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当时教师教学观念的溯源入手,论述民国时期高校老师的上课风格;第二部分对钱穆、夏承焘两位国学大师尤其是对夏承焘的教学风格进行多角度的系统考察;第三部分总结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时期教师教学风格对当下教育工作者的指导意义。
一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生于公元1900年。公元1880——1910这三十年间出生于清末的人当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为了大文学家、大学者、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是一个盛产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的时代,也是大人物风起云涌、接踵而至的时代。陈寅恪曾说,评论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1]279对于夏承焘的教学活动,其教学风格与文化传播价值的判定,也牵涉到环境、背景等方面的因素,因此,知人论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
正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我们认为,夏承焘所生活的清末民国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人民生活最痛苦的时代。而在精神上却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批从旧时代过来的旧文人,正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的上课方式是十分自由开放的,在课堂教学时往往喜欢借题发挥,就某一问题延伸出来,旁征博引、兴发感动,经史百家、琴棋书画、古今中外、道德文章,无所不谈,但与学生们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学术话题。夏承焘上课时气度潇洒,从容自得,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有水流云起,触绪发挥,左右逢源,皆具妙义的境界,在丰富多彩的诗词话题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和醉人的诗情,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启迪,才气干云,令人心折。夏先生的著作别具一格,灵采焕发、新见迭涌,他是词学家,也是词人。在他的诱导和指点下,学生们对词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著述学生们都曾遍读,拳拳服膺之心无日无之。据说夏先生上课时讲到哪里算哪里,任情适性,根本不按教学进度表来上课。这在当时并不是特立独行的现象,如刘文典也是这样,他讲陆机《文赋》时说,这门课可以讲一个星期,可以讲一个月,也可以讲一年,随便他怎么讲。那些民国年间的教师上课时常常会给学生谈一些逸闻趣事,指点一些研究问题的线索,甚至认为“教小孩子读历史,不论小学、中学、大学,要讲故事,讲人物,不能只讲‘封建’、‘专制’等空洞的名词”[3]60,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通过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来谈做人的道理。
当年的大学老师们在讲台上,可谓是儒雅倜傥,潇洒自由,令学生们既敬且爱。象吴梅当年上课时可以仅凭着一卷书,一管笛,一支粉笔,就可以开讲,那时没有多媒体设备,正好可以发挥他们琴棋书画方面的特长,他们上课时常常边讲边吹,边唱边写,黑板上的字迹美观大方,学生们课后都不舍得擦掉。现在的词坛泰斗叶嘉莹就是当年顾随的得意门生,在诗词创作方面颇受乃师青睐,等叶先生自己当老师后,他也有意识地效仿恩师当年上课的风范,在谈及自己讲课风格时,她颇有心得且自信地说:
一般说来,我自己对于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我的疏懒的习性,而且也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以为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我以为就未免要死于句下了。[4]
我们可以从这些前辈学者们的回忆中感受到,那些旧时代的许多知名教授很不遵守上课的规矩。他们想怎么教就怎么教,不用交教案或讲义给领导检查,想骂谁就骂谁,听不听课是学生的自由,现在北京大学还盛传着“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佳话。可学生一旦选修老师的课,坐在他的教室里,怎么讲就是他的自由了。如程千帆晚年回忆道:
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确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斛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5]
通过程先生的回忆,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大学教授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研究专长,各怀绝技,讲起课来也各尽所能,大多不肯受现行体制的束缚。他们上课很不合乎教学规范,不合乎规范化的考试,放到现行的高校体制里肯定要算得上教学事故了,如上引程千帆文中提到的瞿安先生,在另一些学生的记忆中是这样的:
平时考核测验,每月出一、二题目,必令按时交卷。所出的题目,有时是很新奇的,记得有一次题目是《咏日历》,就很为难了我们,大动了脑筋。所交作业,先生无不认真修改。所评分数,不论优劣都是七十分。我们学生背着先生引以为笑话,其实这乃是先生使学生们“先进者不骄,后进者不馁”,正是他教育的好方法。[6]124
我们现在有些高校规定:考试必须至少要有四种以上题型,每门考试课程还要出三套试卷,否则就不合乎规范,要老师重新出过考试题目。民国时的教育不是这样,虽然在学生的记忆中,这些老师的形象不一定完美无缺。可正是有了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或不足,反而让学生们觉得老师不但可敬可信任而且可爱可亲近,是一个有性情、有抱负、有原则又灵活,既理智又热情,既脱俗又入世,既多才多艺又敏锐善感,即使有缺点也是值得敬慕的人。甚至于有时正是他们的那些缺点,让学生们背地里津津乐道,许多逸闻趣事就这样通过口耳相传流传至今,成了北大、清华、南开、复旦、浙大、中大、武大、川大、南大、南师大、华东师大、扬州大学等名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更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都非常优秀,如程千帆、叶嘉莹、任中敏、唐圭璋、万云俊、马兴荣、孙望等都是在那个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那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们也特别热爱他们的老师,如唐圭璋在回忆吴梅时感慨万端:
呜呼,敌人残暴,天胡容之?先生纯儒,天胡忌之?计予从先生十六载,勉予上进,慰予零丁,示予秘籍,诲予南音,书成乐为予序,词成乐为予评。柳暗波澄,曾记秦淮画舫;枫红秋老,难忘灵谷停车。呜呼,而今已矣,旧游不再,承教无期。[6]55
师生感情如此深挚,在我们如今的高校中是十分罕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试从夏承焘、钱穆等民国时期教师的教学经历出发,寻找答案。
二
夏承焘是上世纪的同龄人,他的经历比较单纯,主要就是读书、教书、著书。他的教学思想与讲课风格,与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十八岁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到八十七岁逝世,他一生的主要经历都在教书中渡过,他教过小学(1918年9月至1921年7月,任永嘉县立任桥小学和梧埏小学教师),教过中学(1922年1月至1925年4月,任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陕西第一中学、成德中学教师;1925年9月至1930年6月,任瓯海中学、宁波第四中学和严州第九中学教师);教过大学(1925年5月,任西北大学国文系讲师;1930年7月至1942年2月,任之江文理学院讲师、教授;1942年11月至1952年2月,任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2月至1958年6月,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1958年6月以后,任杭州大学教授。1972年因病退休),他在教师这个岗位上一共工作了54年。[7]
这种经历与大致同时的钱穆有着惊人的相似,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他曾说自己“十七岁中学毕业,十八岁开始在乡村做教师,由民国元年起,可以说一直教到今天,已教了六十七年书,我的生活圈子很狭窄,都在学校度过,我所知有限,只是一些教读经验。……我个人的经验倒觉得教小学时最快乐,教中学时又比教大学时快乐。在中学时学校还像个家庭,一到了大学,就像到了社会,大家都自觉做了教授,社会上的人也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们,而师生的关系却反而疏远了,彼此客客气气。我觉得小学、中学是感情的、生命的;大学嘛,讲学术,有了是非,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多属于知识方面也可说是属于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却不在那里。我读小学的日子距离今天已有七十多年了,但学校的一切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房子是怎样的,大门口在哪里,都清楚记得,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生命。”[3]297-298
其实,钱穆教大学也教得非常出色,据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回忆: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子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的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显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的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8]
夏先生对宾四先生也是十分赞赏的,他的《天凤阁学词日记》里有许多动人的记载,此不赘述。
夏先生的授课风格与宾四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教育家。夏先生的得意门生吴战垒归纳夏先生一生的学术建树有六个方面,即:一、开创词人谱牒之学。二、对词的声律和表现形式的深入研究。三、词学论述。四、诗词创作。五、治词日记。六、培养人才。并对先生培养人才的特色与贡献进行了介绍:
先生的一生经历十分单纯,概括起来就是:读书、著书、教书。他是一位大学问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六十馀年,桃李满天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先生认为是平生最大快事。他热爱教育事业,觉得教书有无穷的滋味,在日记中每有真挚动人的记录。先生还作《教书乐》一文,回顾数十年教学生涯的感想和体会,言之醰醰有味,在丰富的教学经验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和醉人的诗情。听先生讲课,是一大享受。他气度从容,笑容可掬,娓娓而谈,庄谐杂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先生性情温厚,虚怀若谷,见人一善,则拳拳服膺;见时贤之精彩著述,则喜形于色,“恨不识其人”。先生于门下,亦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他送给一位老学生的对联写道:“南面教之,北面师之。”其撝谦善纳如此。对于学生的优点,他总是尽量加以奖勉,且用以自励,在日记中亦有不少感人的记述。先生治学门庑广大,从不以自己的爱好和专长来规范学生,而是因材施教,充分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才性,扬长避短,卓然有所成就。故先生门下,济济多士,略举其著者,如翻译莎士比亚的专家朱生豪,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蒋礼鸿,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戏曲小说专家徐朔方,台湾散文名家琦君(潘希真)等,均亲炙先生而另辟学术新境;传先生词学一脉而卓然成家者则有吴熊和等。[9]
夏先生的经历虽然单纯,但他却是一个能从单纯闲静生活中寻求快乐的人,教书、读书、游山玩水、看戏、著书立说、谈天说地都能给他带来快乐。尤其是,他把教书当成人生最快乐的事,他在《教书乐——三十年教学的体验》一文中说:
我十九岁就开始任教,现在已三十多年了。曾经有几位朋友好奇地问过我:“你为啥坐不厌冷板凳?”虽然我很惭愧,我的教学对同学们没有多大益处,但我对这门工作,却始终感觉快乐;因为我体验得它对我有许多好处:
(一)就治学方面说。从前有人拿老子“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句话,说任教对做学问的好处:一切东西给了他人,自己就少了,或全没有了;只有学问教给人,不但他有得而我无失,并且因经过这一番教授,自己对这门学问更加明白更加深入了,自己的心得也更加巩固了,这不正是“既以与人己愈多”吗?……我以为这是教书的一大乐趣。至若和同学们切磋讨论,有许多“教学相长”之益,那是更不待说的。
(二)就交友方面说。在一切职业里,若论得友之广和得益之大,我以为莫如任教。我们任教一年,可以多交数十位青年朋友;朋友增加,就等于自己的生命的扩大,这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报酬。……
(三)就制行方面说。作为教师而行为堕落的,究竟不大多见,因为你在课堂所讲的话,会使你自己的行为多一个限制,不敢肆无忌惮。……前人有“读书乐”的诗,我说“教书乐”,略约如此。 [10]
我之所以不惮辞繁地引录上述材料,一方面旨在对民国期间成长起来的大学教授们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探求新知之风盛行一时的具体情况作尽可能真实、切合实际的历史还原,以描述清楚当时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主体人格和审美情趣形成的环境和原因;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这一大段文字蕴涵了大智慧,既诚恳实在又生动感人,很能够说明夏先生的教学思想与讲课风格。象这样对祖国的教育事业有着如此充沛的热情、如此通透的见解,决不是一辈子皓首穷经、困死书斋的老朽宿儒说得出来的,也决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奴颜媚骨的新学士子所能道其万一,只有能入复能出的人,既精通传统文化,又吸收新学思潮的通达之士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这是洞察力、才子气、学问家、教育家融合贯通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教学风格。
我们还可以从夏先生的日记及其学生的追忆中探究夏先生的教学思想及其讲课的实际效果,进一步对其“寓教于乐”的教学特点进行系统深刻的把握。夏先生十分喜欢讲课,在日记里,他写道:
讲稼轩词,殊自喜。近年教书,意味醰醰,乐此不疲,可以终身。自念禀气尚能和易,口才虽不大好,亦能舒缓有条理,故幸为学生所容。两年以来,未斥骂一学生。学生亦无非礼相干者。一日无课,辄觉心气不舒,念明日有课,今晚即陶陶动兴。工作与趣味合一,乐哉吾生。曩年一官人怪予能耐苦教书三十年,我诚不觉其苦。以脅肩谄笑为大乐者,安能知我。[11]
正是对教学有着如此的热爱,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举一些学生的深情追忆来还原夏先生的课堂教学实录,吴战垒在《夏承焘先生说词》中谈道:
听夏承焘先生说词,是一大享受。四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说稼轩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夏先生这种授课态度,与另一位授课的任心叔(铭善)先生的严肃正经大不相同。任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的老学生,被夏先生视为畏友,他曾劝夏先生在课堂上要严肃一点,夏先生却说本性如此,无法改变。[12]
吴战垒是夏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与夏先生感情很深,曾在多个地方谈到夏先生的为人与教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致相同的回忆也出现在台湾著名散文家琦君的《三十年点滴念师恩》里:
有一位教文字学的任心叔老师,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时脸上无一丝笑容。他也是瞿师的得意弟子,常常“当仁不让于师”地与瞿师辩论,他认为瞿师对学生太宽容,懒惰学生就会被误了。瞿师微笑地说:“如卿言亦复佳。”他又正色说:“我讲的是做人的道理,你教的是为学的态度。”……顽皮的学生,把一位老态龙钟的声韵学老师比作“枯藤老树昏鸦”,把心叔师比作“古道西风瘦马”,风趣的瞿师则是“小桥流水人家”。以心叔师不妥协、嫉恶如仇的性格,真不知在大动乱期间,何以自处?他又焉能不死呢?幽默轻松、平易近人、谦冲慈蔼,是瞿师授课的特色。因此旁系以及别校同学,都常来旁听他的课。[13]
这里面对夏先生的描述与吴战垒何其相似,如出一辙,可见夏先生在当年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如此地生动感人,反映出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教师“寓教于乐”的教学风格所体现来的教学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方面。尤其是他们的人格魅力,通过学生们的深情回忆,有助于我们重回当时的讲课现场,让当今高校里的学者们深思大学教授的职责何在。
陈平原在《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14]
这段话正可作为夏承焘教学实践的注脚。从中,我们不难在确切理解夏先生教学风格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握当下,建立健全高校文学艺术类通识教育的教学制度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
三
“寓教于乐”的教学风格,对我们当下的教学实践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正如陈平原所说:“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15]陈先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古风也有相似的感触:
目前, 我们有些教师并不能够妥善地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归教学, 科研归科研, 两不搭界; 或者应付教学, 一心投入科研, 为职称奋斗。虽然这与当下的评估机制和导向有关, 但不能不看到这是导致“成果”泛滥、精品奇缺的学术泡沫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教师, 只有将科研与教学需要、社会需要和内在表达的需要结合起来时, 才能生产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至精品。[16]
这段论述太精彩了,可谓是先得我心之论,触目惊心地反映了如今高校的生态环境。我们现在大学老师大多整日忙着做项目、发论文、出专著、评职称及各类奖项,为了这些疲于奔命,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花在教学与学生身上,现实情况令人忧虑。
对比现实,我们更加怀念夏承焘、钱穆等民国时期的先生们了。1986年6月11日,杭州大学举行夏承焘教授追悼会。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扬、杭州大学董事长沈善洪、夏先生的学生蒋礼鸿教授、吴熊和教授、徐规教授等人在追悼会上发言,追忆夏先生作为教育家、学者、词人的一生。其中夏先生的得意门生、传先生词学一脉而卓然成家者吴熊和的发言感人肺腑,令人深思:
夏先生教育我们的,也首先是学行一致的品格志向的陶冶,作为日后为人为学之本。我们常常从夏先生无所拘束的随意漫谈中,听到他深含哲理的议论,领受到有关人生的启迪。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夏先生喜欢看戏,有一出戏,剧中人物一个是王者,冠冕俨然,高坐台中,但终场无所作为,神色索然;一个身份平凡,但一出场满台生辉,精彩的演出吸引人们的目光,谁也不去注意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了。夏先生要我们从这个戏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应该是争角色而不争名位。名位是虚器,角色则贵在实干。夏先生说的争角色,就是要为人民、为祖国作出更大的业绩。夏先生一生淡于荣利,他有一首《鹧鸪天》词说:“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但夏先生为了繁荣祖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孜孜不倦,尽心尽力,贡献了自己的宝贵一生,表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高尚风格。夏先生的这个教诲,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7]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又想起了陈寅恪的感慨:“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1]248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与兴趣合一,人间便是天堂。所以,只有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收到最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课堂上寻找到赏心乐事。而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自己必须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感兴趣,对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感兴趣,尤其是要对自己所教授的对象感兴趣。这些观点,得益于以夏承焘为中心的民国时期教师们教学效果的启示及其教学方法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7.
[3]钱穆等.明报大家大讲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4]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5]巩本栋.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6.
[6]王卫民.吴梅和他的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马兴荣.词学:第二十四辑[J]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9—350.
[8]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51.
[9]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6.
[10]夏承焘.夏承焘集:第八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7—298.
[11]夏承焘.夏承焘集:第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66.
[12]夏承焘.唐宋词欣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3.
[13]琦君.往事恍如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10—111.
[14]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78.
[15]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8.
[16]古风.教学科研结合 创造学术精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笔谈)》[J] .扬州大学学报,2004(3):6.
[17]李剑亮.夏承焘年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274.
永利集团教学研究项目“高校文学艺术类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XGG2013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楹(1976—),男,江西于都人,永利集团yl8cc永利官网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词学研究。
2详参钱志熙《试论夏承焘的词学观与词体创作历程》,《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1期;施议对《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68—486页。